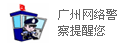一起勞動爭議案件違約責任的確定
王某與某遠洋公司于1999年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王某在公司中從事船員工作。合同中約定,任何一方造成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應承擔違約責任。隨后公司根據其單位的特點,在2005年10月制定了自己單位內部的管理規定,對違約責任的承擔方式和數額做出了明確的規定,該管理制度經公司職工代表大會討論通過,并在公司的局域網、內部刊物上予以了公布。后王某自2008年2月,未上崗工作。隨后,公司多次發電給王某,要求其到公司上班,逾期按曠工處理。但王某一直未到公司報到,2008年4月公司以其曠工為由,對其做出除名處理,與其解除了勞動合同。王某按公司的管理規定向公司交納了違約金。后,王某要求公司退還其交納的違約金,成訟。
本案爭議的焦點是某遠洋公司因王某曠工與其解除勞動合同后,是否可以依據與其簽訂的勞動合同及其該公司制定的規章制度收取王某的違約金。
一種意見認為,某公司與王某在勞動合同中雖有“任何一方造成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應承擔違約責任。”的條款,但按照《勞動合同法》的規定,某公司與王某在勞動合同中約定的違約責任條款無效。且某公司隨后制定的內部規章制度,雖對違約責任的承擔方式和數額作出了具體明確的規定,但某公司無法證明對王某進行了告知,也無法證明王某已知情。因此該規章制度對王某未生效,對其也沒有約束力。故認為某公司依據與王某簽訂的勞動合同及本公司制定的規章制度收取王某的違約金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王某的請求應予支持。
另一種意見認為:某公司與王某在1999年簽訂了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該合同是在雙方自愿的情況下簽訂,并且不違反當時相關的法律法規規定,因此應認定勞動合同合法有效。在勞動合同中雙方約定的“任何一方造成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應承擔違約責任。”雖然對違約責任的承擔方式沒有明確約定,但在某公司隨后制定的內部規章制度中對違約責任的承擔方式及數額均作出了明確的規定。該內部管理規定不違反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及政策規定,且經過了某公司職代會通過,并在某公司網站、內部刊物上均予以了公示。因此,可以認為該內部規章制度對某公司的全體員工有效。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九條“用人單位根據《勞動法》第四條之規定,通過民主程序制定的規章制度,不違反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及政策規定,并已向勞動者公示的,可以作為人民法院審理勞動爭議案件的依據”的規定,某公司依據與王某簽訂的勞動合同及本單位制定的規章制度收取王某的違約金具有法律依據。王某應當承擔違約責任。
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
用人單位為了實現規范化管理,保證單位各項勞動任務的順利完成,同時保障勞動者依法享有勞動權利和履行勞動義務。往往都會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制定出適合本單位的規章制度。但的確不是用人單位制定的所有的規章制度都會對勞動者產生效力,成為人民法院審理勞動爭議案件的依據。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9條規定,只有符合以下條件的規章制度才能成為人民法院審理勞動爭議案件的依據。
首先,該規章制度應通過民主程序制定。即必須通過職工代表大會或其他民主程序通過。
其次,該規章制度應當合法。所謂合法,即不違反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及政策規定。
最后,規章制度應當向勞動者公示。規章制度是否公示對勞動爭議案件的處理影響極大,可能直接關系到勞動爭議案件的勝敗。實踐中,規章制度的公示方式很多,用人單位可以選擇適合自己單位情況的公示方法。比如,將規章制度在企業內部進行學習、培訓;簽訂職工手冊;在勞動合同中約定;在網站上公布;在單位的公告欄、宣傳欄內張貼等多種方式。但一定要注意保存公示的證據,盡量采取易于舉證的公示方法。否則一旦認定未經公示將對勞動者不產生約束力。
《勞動合同法》第四條對此也進行了規定,即“用人單位應當依法建立和完善勞動規章制度,保障勞動者享有勞動權利、履行勞動義務。用人單位在制定、修改或者決定有關勞動報酬、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勞動安全衛生、保險福利、職工培訓、勞動紀律以及勞動定額管理等直接涉及勞動者切身利益的規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項時,應當經職工代表大會或者全體職工討論,……用人單位應當將直接涉及勞動者切身利益的規章制度和重大事項決定公示,或者告知勞動者。” 可見,《勞動合同法》又從法律的層面對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予以了確認。
縱觀本案,王某與某公司是1999年簽訂的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該勞動合同中約定,“任何一方造成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應承擔違約責任。”按照當時的法律法規,用人單位與勞動者之間可以在合同中約定違約責任。新的勞動合同法雖然在第二十五條中規定,“除本法第二十二條和第二十三條規定的情形外,用人單位不得與勞動者約定由勞動者承擔違約金。”即除服務期和保密情形外,禁止約定由勞動者承擔違約金。但《勞動合同法》于2008年1月1日施行,按照法律一般不溯及既往的理論,《勞動合同法》施行前已依法訂立且在勞動合同法施行之日存續的勞動合同,只要不違反合同訂立時的法律法規,在勞動合同法施行后,即使部分條款不符合勞動合同法的規定,也應當視為有效,應當繼續履行。另外,考慮到遠洋公司的行業特點,公司定期為船員支付培訓及辦證等相關費用,及遠洋船員緊缺等綜合因素,勞動合同中的違約責任條款合法,應繼續有效。
本案中某公司2005年10月制定的內部規章制度雖是在王某與某公司簽訂勞動合同后制定,但其系經某公司的職工代表大會討論通過,也不違反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及政策規定并在某公司的局域網及內部刊物上予以了公布。因此可以認定該規章制度對某公司的勞動者已經進行了公示,履行了對單位職工的告知義務,對全體職工發生了效力。且該規定制定時,王某在該單位正常工作,故應推定王某對該管理規定已知曉。若再由單位證明王某知曉該規定,對單位是不公平的,也會加重單位的舉證責任。故,王某應依據與某遠洋公司簽訂的勞動合同及該公司制定的規章制度承擔違約責任,支付違約金。
更多勞動法內容盡在勞動法律網http://m.43667.cn
熱點文章點擊
- 01工傷賠償標準2015
- 02工傷認定的情況、申請時間
- 03病假的天數是怎么計算的
- 04最新勞動仲裁申請書
- 05辭職的流程
- 062015年生育生活津貼標準如何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