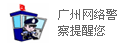勞動調(diào)解相關(guān)立法草案的不足和建議
從內(nèi)容來看,《勞動爭議調(diào)解仲裁法》草案有了實質(zhì)進步,有助于勞動關(guān)系的維持。但是,相關(guān)規(guī)定仍然存在體系化的矛盾,過于刻板,缺乏對勞動者選擇權(quán)的尊重。
(一)個別勞動爭議調(diào)解制度設(shè)計的不足和建議
首先,個別勞動爭議的強制調(diào)解有悖自愿原則。調(diào)解如果不是基于當事人合意而進行,調(diào)解成立的可能性就會降低,只會徒然浪費雙方當事人與主管機關(guān)的時間和資源,況且又有干預(yù)和妨礙勞動者行使訴權(quán)的嫌疑。
其次,不區(qū)分勞動爭議性質(zhì)的強制調(diào)解難以發(fā)揮有效作用。勞動調(diào)解制度并非萬能,應(yīng)當合理確定勞動調(diào)解的意義和目標,有所為而有所不為。勞動調(diào)解旨在通過調(diào)解不傷和氣地解決糾紛,從而為勞動關(guān)系的持續(xù)奠定基礎(chǔ)。如果像在仲裁和訴訟中雙方都撕破了臉,勞動關(guān)系談何維持。這也是勞動仲裁和訴訟關(guān)于維持勞動關(guān)系的裁判難以執(zhí)行的原因。而事實上,多數(shù)勞動爭議都因離職或解雇而引發(fā),因為在勞動供給大于需求的時代,正常勞動過程中,即便有糾紛,勞動者為明哲保身,常常無奈地接受很多不公平待遇,而離職或遭解雇時則會將積壓的矛盾激發(fā)。因此勞動調(diào)解應(yīng)當準確界定勞動爭議的性質(zhì),區(qū)分便于調(diào)解和難以調(diào)解的勞動爭議事項,對辭職引發(fā)的勞動報酬和社會保險等爭議應(yīng)當允許直接提起仲裁或者訴訟。
其實,要解決以上個別勞動爭議的調(diào)解問題,只要將選擇調(diào)解的權(quán)利單方賦予勞動者即可。畢竟是否維持勞動關(guān)系主要取決于勞動者的態(tài)度,如果勞動者認為還有維持勞動關(guān)系的必要,則其可以選擇調(diào)解化解矛盾、解決糾紛。而如果糾紛產(chǎn)生于辭職或者解雇,那么勞動者應(yīng)當有權(quán)提起仲裁或者訴訟。這樣既避免了企業(yè)惡意提起調(diào)解以拖延時間的弊端,也充分尊重了勞動者的選擇權(quán)。
(二)集體合同調(diào)解制度設(shè)計的不足和建議
草案對集體合同爭議采取了非強制性調(diào)解的規(guī)定,即對于集體合同爭議,草案采取了約定仲裁,否則訴訟的安排。這樣的考慮似乎有些欠妥。如果說和諧勞動關(guān)系是博弈的結(jié)果,那么集體合同關(guān)系到勞動者的基本保障,它是個別勞動合同的底限。因此集體合同在穩(wěn)定勞動關(guān)系中的重要意義不言自明,而相關(guān)爭議則基本都是群體性爭議,處理不當容易激發(fā)矛盾。為此,很多國家規(guī)定了強制仲裁、國家特別機關(guān)強制調(diào)解等制度。比如,美國2003年1月針對農(nóng)工出臺了“強制調(diào)解法案”。根據(jù)該法案,如果農(nóng)工工會不能在180天內(nèi)和用人單位達成集體合同,調(diào)解員將有不超過30天的時間進行調(diào)解,如果不能達成調(diào)解協(xié)議,則該調(diào)解員必須在21天內(nèi)提出相關(guān)條款和最低工資建議。農(nóng)工關(guān)系委員會全面審查該建議,并發(fā)布最終條款。一旦發(fā)布最終條款,任何一方都可以在60天之內(nèi)請求法院強制執(zhí)行。在勞動者權(quán)利保護不足的現(xiàn)狀下,充分保護勞動者基本權(quán)利的類似制度應(yīng)當予以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