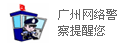本案被告的抗辯事由能否成立
[案情]
原告湯、劉系夫妻,1979年1月生育一子湯寬。2001年1月,被告岳均與其夫葉沖購買了川F31877號大貨車,從事運輸業。同年9月,受被告岳均之夫指派,二原告之子湯寬駕駛該川F31877號大貨車同葉沖赴廣東運輸貨物,該月4日13時20分許,湯駕車行致廣汕線48公里處,與牌號為湘M60550大貨車相撞,湯寬、葉沖當場死亡,湘M60550大貨車駕駛員棄車逃逸。交警部門認定逃逸者負本次事故的主要責任,湯寬負本次事故的次要責任,葉沖無責任。2002年1月24日,原告湯繼團與被告岳均在四川省彭州市蒙陽法律服務所組織下,達成了互不追究(民事)責任的協議。后被告岳均代表雙方家屬前往廣州向湘M60550車主及駕駛員要求賠償未果。同年5月17日,岳均將保險公司理賠款5100元,轉付了二原告。現二原告涉訴要求被告按雇主責任賠償,被告則以雙方以達成互不追究責任協議拒絕賠償。
[判決]
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認為,二原告之子湯寬受被告岳均夫婦指派駕車途中因操作不當與M60550貨車相撞,發生事故,主觀存有過錯,應承擔一定責任。交通管理部門劃分的事故責任不無不當,應予采信。湯寬死亡后,就民事賠償問題,二原告在向直接侵權人主張權利不暢時,轉向湯寬雇主被告岳均要求賠償在法律上是無限制的。關鍵是湯是否在履行職責中受侵害。經查,湯駕車系運輸的為被的貨物、出事前,另一雇主在車上跟隨,行走路線亦未超出原定方向,故應能認定湯寬系在執行雇傭工作的過程中形成的損害,作為雇員湯寬的直系親屬有權要求雇主承擔賠償之責。然事發后,二原告就該損害后果的處理及如何向第三人主張權利與被告達成了互不追究責任的事后協議,協議內容清晰完整體現,協議條款能反映雙方合意的過程及最終形成的一致意見,協議內容未見違反相關強制性規范,又無損害他人利益條款,該協議合法有效,依此協議二原告不能在向被告主張權利。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八條第一項之判決:駁回二原告的訴訟請求。
[評析]
(一)關于本案責任的認定。
本案涉及兩個層面的法律問題,一是在原告之子湯寬應與被告之間存在雇傭關系的情況下就其因從事勞務而死亡時,因死亡所生之損害雇主應否賠償。在一般情況下,死者之近親屬應獲賠償并無疑問,然本案之特殊情況在于:其一,湯寬應之死亡與其自身之過錯行為有關,進一步言之,相對于被告而言,湯寬應之死亡系因其自身原因,即過失行為而致其死亡;其二,因湯寬應之過失行為,不僅導致其自身身亡,還導致雇主之一的葉定沖死亡。在如此特殊情況之下,原告應否獲得賠償?有不同觀點,有人認為從民法中的因果關系的角度選擇賠償主體。湯寬應之死亡系與湘M60550貨車相撞直接造成,按劃定的事故責任,由加害人賠償,雖行為人無法查找,原告的救濟暫時無法實現,但亦不能轉向請求雇主賠償,因雇主在交通事故中無過錯,不能加重雇主責任,最高人民法院雖出臺了關于人身損害賠償新的司法解釋,就有關雇主責任有了新的規定,但該案系在解釋實施之前受理,不能適用該解釋,故應按原規定調理該案。但筆者認為本案涉及不真正連帶之理論,這一理論我國民法上未見表露,理論界近年來論證較多,但實務界觸及較少,傳統甚至予以排斥,從而影響案件的結果。
不真正連帶是指多數債務人就基于不同發生原因偶然產生的同一內容的給付,各付全部履行之義務,并因債務人之一的履行而使全體債務人的債務均歸于消滅的債務。按此定義理解不真正連帶亦屬賠償權利人的選擇權范疇,但其與我國合同法規制的責任竟合,即請求權競合是有不同的理論基礎。合同法列舉的責任競合是指同一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對同一法律后果享有數個請求權。二者關鍵區別為前者權利人的請求權系基于不同的原因而形成,后者是源于同一債權債務人間就產生的法律后果存有幾種不同角度的請求權。不真正連帶并不是民法上意義的連帶責任,雖然它們均有債務人眾多、給付內容基本相同、因一給付而使全體債務消滅等較多雷同之處,但二者亦有顯見之別:
1、引起的原因力不同。連帶責任一般產生于共同指向的原因,即同一事實;然不真正連帶具有不同的發生原因,要求當事人間的債權、債務關系必須基于不同的法律事實而生成。
2、目的不同。連帶責任具有共同目的,事先的意識聯絡及共同追求為其顯要標志;而不真正連帶則無共同目的之特征,給付內容的等同純屬偶然,行為人間更無意識關聯。
3、規范設置不同。民法中的連帶責任實行法定主義及當事人約定主義,禁止亂連帶;而不真正連帶生成的系法官在個案中根據不同的因果關系引生的法律關系競合情形而確認最有利于救濟權利人途徑。無須法律列文規定。各國立法亦無明文規定,然均承認此項制度。我國法院依此科學的制度裁判的案件頗多,不乏應鑒。近期最高審判機關在關于侵權歸責的司法解釋中明確了該制度,實屬突破。具體本案原告之子湯寬應生前與被告夫婦建立了雇傭合同,且事發時原告之子湯寬應正在履行雇主交辦的運輸任務,途中與第三人發生交通事故。從這一事實揭示原告之子湯寬應與被告形成了雇傭關系的合同之債,而原告之子湯寬應在履行職務中與不明身份的第三人發生交通事故,雙方又形成侵權之債,完全符合前述不真正連帶之債的特征,原告可以此理論請求雇主賠償。這并未加重雇主之責,雇主賠償后可向終局責任人追償,這點并未違反民法通則的精神,相反更符合民法中有關充分救濟權利人的利益,懲罰加害人過錯的原則。這與新的司法解釋是否生效并無多大牽連。另須說明,不真正連帶之債同樣適用過失相抵之原則,即死者對于死亡之后果存有過失,可減輕雇主的賠償責任。本案合議庭也是基于這一原由,確定了被告的賠償責任。
(二)關于和解協議的性質。
損害結果發生后賠償權利人即原告,與賠償義務人即被告達成互不賠償的協議。該協議從時間看系在結果發生后形成,筆者認為該協議應歸屬于和解協議范疇。所謂和解,是指當事人約定在相互讓步,以期終止爭執或排除法律關系不明確之狀態的合同。按照合同自由原則,當事人可以通過合同產生、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也可通過合同在原債權債務基礎上設立新的債權債務。和解協議并非對原債權債務的變更或補充,而是新的獨立存在的有名合同。原、被告間的事后協議是否構成和解,須從三個方面分析界定:1、協議雙方存在著一定的法律關系,即相互賠償義務的關系,而且雙方就此種法律關系有爭執或說有發生爭執之可能;2、協議雙方訂立這種協議目的,主觀上就遇要終止或防止爭執之發生;3、雙方相互作出讓步,即雙方約定互不追究責任。依上述規則衡量原、被告間協議,應屬和解性質。
(三)關于和解協議的效力。
有人認為依合同法第53條規定,合同中關于造成對方人身傷害的免責條款無效之理解,原、被告之間就人身損害賠償責任的排除協議,違反了上述強制規范,該協議無論何時形成,均應產生無效之后果。我們認為只要是雙方真實的意思合意,協議內容不違反法律和社會公共及他人利益,就應具有法律效力。依此原則揭示原、被告事后成就(和解)協議應為有效,而合同法53條規定的免責條款效力問題,其法意指雙方在合同中約定的為免除或限制一方或雙方未來責任,系事先預想的責任與事后的和解協議有明顯區別,此點不在深述。從列舉的(和解)協議顯示,原、被告間簽訂的(和解)協議,還透視如下效力:
一是確定了法律關系。因和解之訂立,當事人終止或防止法律關系之爭執,以相互讓步而鎖定法律關系。當事人已喪失就同一和解事項再行主張的權利,且各自負和解確定的債務履行之責,從法律關系確定而言,和解有一種形成之效力。原、被告間曾有相互債務,即相互承擔賠償責任,但因和解協議的成立、生效,則雙方相互免除了債務,這是一種處理行為(債務免除),從而形成了一種新的法律關系。由于就的法律關系的形成,縱使以后原、被告之一方認為自己本不應向對方承擔責任,亦不得向對方主張。
二是和解于當事人的債權,有創設之效力,原債權因和解而消滅,同時因和解而取得新債權,日后縱有與事實不符之確信,亦不得推翻。
本案判決基于和解的上述效力,作出認為原告要求被告承擔雇主責任已違背了雙方的事后協議,故對原告之訴訟請求不予支持的結論,是妥當的。
上一篇:通過本案看雇傭關系的非盈利抗辯
下一篇:該案中人民調解協議應否撤銷
熱點文章點擊
- 01工傷賠償標準2015
- 02工傷認定的情況、申請時間
- 03病假的天數是怎么計算的
- 04最新勞動仲裁申請書
- 05辭職的流程
- 062015年生育生活津貼標準如何確定